中国风席卷欧洲?历史上西方人竟这样山寨中国文化
日期 | 2018-12-04 来源 | 搜狐艺术从17世纪始,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曾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们、传教士们的有力助推,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从17世纪开始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所谓的中国风尚趋之若鹜;中国风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这场中国风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顶峰,直到19世纪才逐渐消退。华托、布歇、皮耶芒、齐彭代尔、钱伯斯、瑞普顿等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大师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设计师、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中式建筑、艺术品和工艺品为后人记录和保存了它席卷欧洲大陆的深刻痕迹。

《圣厄休拉和她的少女》( Niccolò di Pietro ,1410),画面中女性圣徒所穿长袍,缀满了凤凰图案,显而易见受到了东方丝织品的影响。
“中国风”作为时下文化领域的流行词汇在国际时尚界可圈可点,许多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东风西渐”的结果。事实上,早在百年之前,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就刮起了“中国风”(chinoiserie)。然而,当这些带着中国印记的文化产品舶来中国,许多国人却只是惊叹于其中的异国情调。
西方艺术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表现形式由结构线条转向书法线条,前者重视线条的隐匿和对现实的再现,后者则重视线条本身的品质和神韵,倾向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特质更多地表现观念的不稳定性与主观性的一面,这一点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20世纪最伟大批评家罗杰·弗斯认为,西方人对东方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的吸收导致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转型。

1592 年,满载着东方珍稀物品的西班牙大帆船“圣母号”被英国海盗船劫持到达特茅斯港。
因为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的这种姻缘关系,中国绘画得到全世界的推崇,以致于二十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人借助西方人才重新发现和体认了自己的传统价值。
到了2000年后,西方人又开始发掘“意境”等中国古典趣味,欧洲人还因此建立了美学学科。而国人经济上的后继者地位却导致了文化上的不自信,正如英国不规则园林本是中国的专利,而英国人通过名之为现代园林,便轻易地将英国的迟滞状态转化为先锋地位,而将中国原来的优势解释为它的落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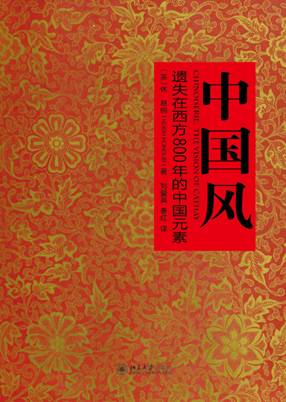
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休·昂纳的《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以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细腻笔触和艺术家的敏感梳理了西方文化中中国风的兴起、兴盛及其衰落、流变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诚如作者所言,在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神州并非真实的场景,而仅仅是一个幻境;虽然不乏中国元素,但像哥特风一样,中国风归根结底仍是一种欧洲风格,它表明的是欧洲人对一个在距离上遥远、心理上神秘的古老国度的理想化的认识和理解,而非某些汉学家所言,仅仅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
只有把中国文化放在西方历史当中审视它,才能超越我们对“中国风”碎片式的了解。原书作者昂纳作为文学专业出身的美术爱好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梳理了西方文化中中国风的兴盛、衰弱及流变的复杂历史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意义深远。
以下摘选书中的精彩篇章。
织工的牢骚
“可恶!穿着毛衣!这会让一个圣人发怒的”。
(这是可怜的那纳西萨说的最后的话)。
“不,就让一些漂亮的印花棉布和布鲁塞尔蕾丝
裹住我冰冷的四肢,遮住我没有知觉的脸庞”。
亚历山大·蒲柏:《道德论》(Moral Essays )第一篇信札,1733年

14世纪卢卡生产的丝绸,上面出现了中国的“百鸟之王”凤凰和瑞兽梅花鹿的形象
17世纪后期,进口到欧洲的东方纺织品数量巨大,而且大受上流社会的推崇。但在法国和英国纺织工人那里,这些东方纺织品却明显地遭到了冷眼歧视,因为这个新风尚流行起来快得惊人,现在已威胁到他们的生计。早在17世纪50年代,红衣主教马萨林(Cardinal Mazarin)似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危险,并且鼓励生产“中式织法的哔叽”,以帮助法国的产业与其东方的对手进行竞争。到了1683年,这种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以至于卢瓦开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法国的织工。暹罗的大使带来了成捆的中国珍贵物件,将之作为礼物赠送给皇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他们的到来让这些措施显得更加有必要了。原因就在于,虽然说仿照大使的长袍发明出的一种叫做暹罗绸的衣料让纺织工人获得了一些利益,但这又因为使团进一步刺激了进口东方纺织品而被抵消掉了。于是便对从荷兰和英国进口的所有纺织品(不论是在那两个国家还是在东方生产的)课以重税,同时禁止进口印花布料(印花布)。薄纱织物和白色印花棉布如果不是在法国纺织的,就不在受限之列,而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则享有特许权。

17世纪巴黎生产的中国风真漆橱柜

收藏于罗浮宫博物馆的美第奇陶瓶
这时,在财政部和该公司之间开始爆发一场小规模的战争。1 7 0 0 年,当宫廷还陶醉在中国国王假面舞会的时候,该公司的商船“安菲特律特号( Amphitrite)”满载而归,这些琳琅满目的外国商品就是第一批直接从中国进口到法国的商品。167箱瓷器,数不清的一捆捆丝绸、薄纱、缎子以及数量不明的漆器装满了商船的货舱,商船抵港让宫廷开心不已。法国的手工艺者则不然,他们的代言人给印度公司的董事长发去了一封措辞犀利的信函。他这样写道:做柜子的工匠、陶工还有纺织工人对于该公17世纪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到英国的数量巨大的商品深感震惊。虽然他也承认,为了收藏家的利益,他们有权利把最精美的东方器皿带到法国来,但是他也对进口劣质商品导致其在市场上与法国产品竞争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这起事件以及类似事件的结果就是,丝绸和印花布料的进口在1714年遭到禁止,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由印度公司负责进口。这些限制使得东方纺织品无法流行起来,从而有利于本国丝绸的生产。到了1735年,这一做法又回到了起点:这个时候,黎塞留公爵(Duc deRichelieu)盛赞一些印度锦缎产品,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它们把法国同类产品模仿得那样完美——“连行家也会在这上面看走眼”,他补了这么一句。在英国,因进口东方纺织品而引起的纠纷还更加严重。每年自东方回国的英国商人人数不断翻新,他们带回的商品充斥着各个市场。在17世纪结束之前,纺织工业已经不胜其苦。1690—1700年间,坎特伯雷用于生产的丝绸织机数量锐减。同时,许多史派特的织工都丢了饭碗,被迫从事不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1700年,议会启动了一些限制措施,不但禁止进口,而且也禁止穿戴印度白棉布和印花棉布。这项动议让时尚界感到害怕。塞缪尔·佩皮斯说道,“我们的议会公开声称,决心禁止穿戴任何印度丝绸和白棉布。如今,在我们的英国女士们为此感到十分忧虑的情形下”,佩皮斯因此提出以下疑问,索尔兹伯里女勋爵(Lady Salisbury)是否还会认为从罗马回到伦敦是值得的。

乔凡尼·贝利尼和提香的画作《诸神之宴》(局部),位于画面后排中心位置的女神和男神手上和头上的是中国明朝样式的瓷碗。
这条法律的一个后果是,走私成了一项获利极高(如果也有危险的话)的生意。正如他们在《织工的抱怨》中唱到的那样:
商人们全部都在走私,
贸易完全就是变戏法,
由花招巧妙的家伙经营。
1708年,丹尼尔·笛福(他是一个极端且不讲道理的、憎恶中国的人)仍在抗议,说虽有议会的限制措施,但对于毛织品和丝绸贸易的保护还是不够。可是,人们对于白棉布和印花棉布的热情持续不退,这就对历史悠久的英国纺织工业造成了损害。直到最后在1719年,史派特的织工发生了暴动。他们疯狂地穿越整个城市,只要发现一位女士,他们就会将镪水洒到她的衣服上。许多暴动者被抓了起来,并上了颈手枷。为表蔑视,一些鲁莽的妇女全身上下穿着精美的白棉布就出了门。结果,那些逃避了惩罚的织工就从背后把她们的袍子给撕碎了。在地方上也爆发了类似的暴力事件。议会因此被迫再次采取行动,并在1721年将禁令从东方纺织品扩大到了所有的棉质商品。女士们有两年的宽限期,但1722年圣诞节后就被禁止用棉布做衣服,或者是做家居装饰。很难讲这项法律执行起来到底有多么严格,但是它好像救助了羊毛和丝绸产业。1736年,这项法律有了点松动,但即便是这个时间之后,印度印花布和中国刺绣也只有靠走私者才能运进英国。

托马斯·布朗爵士,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医生、作家。

英国黑漆橱柜,17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