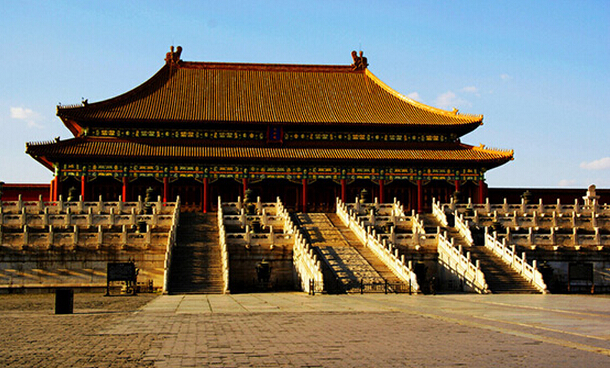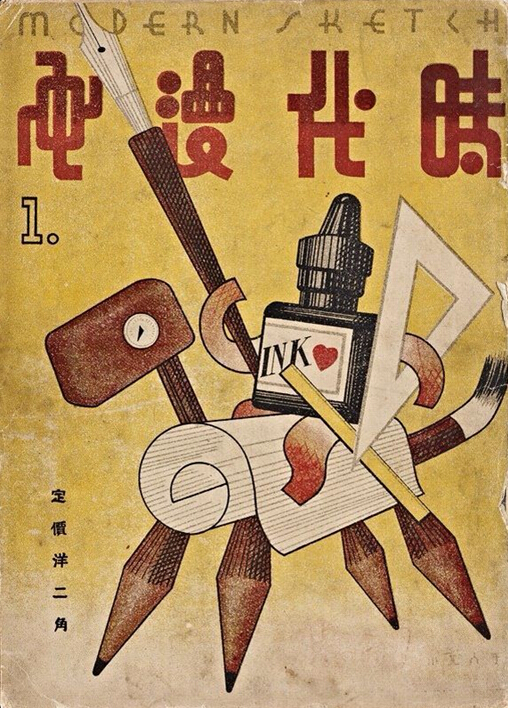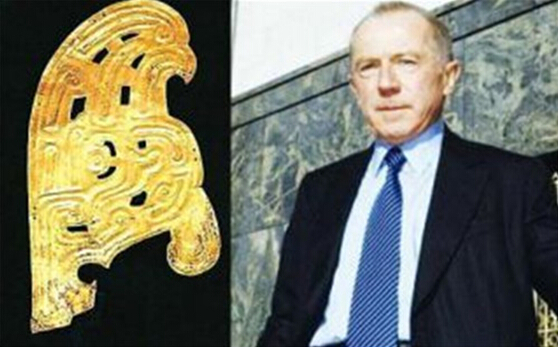上海南外滩“涂鸦艺术长廊”
最近上海的一堵墙很火,频频见诸报端——2015年初上海康定路600弄老城区的拆迁墙上被法国街头艺术家马兰一夜之间绘成了“涂鸦墙”,但随即便被管理部门铲为平地。时隔几个月之后,马兰的“涂鸦墙”又出现在海金山区枫泾古镇的小巷。多姿多彩的“涂鸦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模仿学习者有之、驻足拍照留念者有之,当然,此中也不乏扮演城市秩序管理角色的制止者······可以说,“涂鸦墙”出现在哪里,争议、议论就便出现在哪里。所以,不免要问一面面创意无限的“涂鸦墙”缘何如此招人“羡”、惹人“嫌”?
城市个性的“引领者”还是秩序的“破坏者”?
涂鸦墙,顾名思义就是在墙壁之上胡乱涂画,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涂鸦墙是青年人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但其常出现在城市贫民区,又往往带有帮派以涂鸦墙划定势力范围的性质。如美国“最后幸存者”“18街”“前卫”“拉美王国”等有名的黑帮组织均有自己的涂鸦标识。这些标识被图画在街区或地铁线上,一旦有其他组织入侵领地,则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一场“帮派之战”的械斗,可以说,涂鸦在其诞生源头上充满着野性和血腥。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认识的转变,附着在涂鸦之上的野蛮和暴力色彩逐渐消退,涂鸦作为一种城市文化艺术在世界传播,成为城市张扬个性的一种方式。其实,马兰在上海康定路600弄和海金山区枫泾古镇的涂鸦墙,并不能代表上海,上海涂鸦墙的典型代表是位于莫干山路的M50、洛克公园涂鸦墙、华池路弄堂、南外滩老码头、上海理工大学军工路校区和汶水路的涂鸦墙。
上海南外滩无疑属于城区的核心地带,是上海CBD的核心拓展区,而在此处意大利的艺术家RenatoDaina创制的300多米的涂鸦墙上,涂鸦的形象或古怪,或调皮,或刁钻,或诡异,或搞笑,那嘴角露出的鬼魅笑容似乎在暗示着上海这个志在打造“国际时尚范”的同时,也不应忘却文化性情的荒诞与乖张。而城市正是有了对多元文化的接纳和包容,才有可能为城市注入“追求卓越”的基因。
其实,世界知名城市的涂鸦墙已经成为这些城市颇具个性和创意化的标志。伦敦东区、纽约春天大街、巴黎左岸、柏林的柏林墙遗址等,均有大量的题材多样、形式各异的“涂鸦墙”。在笔者看来,“涂鸦墙”是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是城市年轻、富有活力的象征,引领着城市个性的张扬。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城市都能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涂鸦墙”。上海的“六大涂鸦墙”名声在外,早已具有地标性的意义,但新被涂鸦的康定路600弄墙却难逃被拆除的命运。所以,在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城市提出的培育“海纳百川”“开明睿智”等诸如此类的城市精神是否是一种“虚伪的虔诚”?已存在十年之久的合肥红星路闹市口的涂鸦被城市管理者“叫停”,理由是墙壁涂鸦有违“街道宣传”;华中科技大学里“东九墙”涂鸦墙的学生涂鸦被保卫处制止,理由是“抒情应当有边界”;北京樱花小街南侧曾被誉为“北京涂鸦地标”也未能逃脱屡次被刷掉的命运。
在城市秩序的维护者们看来,这些涂鸦画犹如泼墨,破坏了城市街道的整洁和美观。这无可厚非地构成了整治涂鸦墙的理由,部分涂鸦者爱好者曾一度企图将上海世博会古巴馆内的馆签名墙发展为涂鸦墙的做法就貌似不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秩序的维护者可甩掉“虚伪的虔诚”的质疑,理直气壮地将涂鸦者及涂鸦墙视为城市秩序的“破坏者”。
“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
无论是将“涂鸦墙”定性为城市个性的“引领者”,还是“破坏者”,其实在异常喧哗的争议之下内涵着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即城市“涂鸦墙”的治理是应采取“堵”还是“疏”的方式。“堵”“疏”之争历来是困扰我国城市治理的问题,方式不当以粗暴的方式“堵”,则人们怨声载道;而毫无原则地任其发展,则又会泛滥成灾,人们颇受其累。台湾彰化鹿港的摸乳巷内的涂鸦,因常有涂鸦者冲着“摸乳巷”的名头兴致而来,在墙壁上涂画写不健康的文字和图画,引发周围群众的反感和投诉,以致“逼迫”小巷管理者做出了不再设“涂鸦墙”的决定,但这却丝毫未能削减涂鸦者的涂鸦“热情”。与之相反,武汉黄鹤楼公园为解决游客乱涂、乱画的问题,设立的“电子涂鸦墙”却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游客胡乱涂画给园区治理带来的压力,但“电子涂鸦墙”20万元一台的成本也制约着这一“疏”的方式的大面积推广。
由此两个案例相较可见,“堵”虽在理论上可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收效短暂,也易留下“不解风情”的口实;“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也最能考验治理者的智慧、财力和魄力。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说“堵”与“疏”还是站在问题的外围来审视这一问题的话,那么,当我们变换一个维度,将思考的重心转向那些手持画笔的涂鸦者自身,设想只有涂鸦者的涂鸦创作内容不含血腥、色情和暴力,而又能以一种自觉和维持城市秩序的心态进行涂鸦时,涂鸦才不会成为人们禁忌或厌恶的艺术。